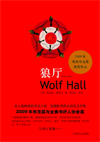亨特妻子:我与保罗最后的日子
luyued 发布于 2011-05-26 09:09 浏览 N 次2004年的五月,我与我的王子在Jamaica举行了一场童话般的婚礼。那时我已经认识保罗-亨特七年了,第一次见到他时,他已经是个斯诺克球手,刚刚18岁。他有个绰号是“台球贝克汉姆”,他有着帅气的面庞和金色的长发。25岁那年,他第三次夺得了大师赛的冠军,而且到那时为止,除他之外只有两名球员取得过这样的成就。 结婚后不久,我曾在日记里这样写到:“保罗和我是如此的相爱,如此的幸福,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对。”但是就在那年年底,保罗便开始断断续续地受着疼痛的折磨。到了05年年初,疼痛开始变得持续不断,因此他去看了医生,并被诊断为可能患有阑尾炎。 经过对他腹部的扫描,结果显示保罗的阑尾并没有问题,不过他的下腹部却有六个囊肿。医生对他采取了腹腔镜检等一系列检查。结果显示,那些囊肿实际上是肿瘤,而且是恶性的。最后的治疗方法是进行化疗,三天一个疗程,要进行三个疗程。我仍然可以清楚地记得,在知道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后,我们是怎么回的家。 保罗的脸是苍白的。那晚,我们在一起,他问了我所有在医院没有问出口的问题,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他说:“林希,我是不是得了癌症?”如果是你,你会怎么回答?我拉起他的手,凝望着他的眼睛轻声地说:“是的宝贝,你得了癌症。”那一刻,他看上去像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。我抚摸着他的手,抱着他,在他耳边说道:“我们会将一切都解决的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” 我记得他几年前曾经说过他可能会得癌症。电视上有一个宣传片上说,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可能得癌症。保罗说:“我就是其中一个,我就是三分之一中的那一个。”现在想想,真的有些不可思议。 两天之后,保罗出发去参加中国公开赛。这是几个月之前就安排好的,因此他必须要离开一个多星期,而他则希望将这当作一次平常的出行。很意外,他打进了最后的八强。当他四月初回来的时候,我们第一次拜访了癌症专家。 那位专家也并不确定保罗到底得的是哪一种癌症。他怀疑有两种可能,一个是一种在睾丸上的胚组织瘤,而且相对比较容易医治,有90%的成功率;另一个可能是内分泌癌,治愈几率要小得多,只有大概三分之一。 仔细的检查后,胚组织瘤被排除了,医生通知了我们一个坏消息,确诊结果很有可能是内分泌癌。他还给我们看了腹腔镜检的片子。那里看上去有200个肿瘤,而不是六个。他们粘连在一起,形成许多令人不忍目睹的肿瘤团。 保罗说,当他知道那些东西就在他体内时,他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。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,只管问着问题,记着笔记。但是我同时也变得茫然了。休克、肿瘤、癌症、恶性、化疗,这些词实在太可怕了,而且我实在无法将这个词与我的心爱之人联系起来。 两个星期后,05年世锦赛将在谢菲尔德开始。按照约定,保罗将在那之后开始他的第一次化疗。而且我们都一致同意,让保罗尽可能心无杂念地延长他的运动生命。 如果是在童话里,保罗应当赢得最后的冠军才是。但现实的生活却并不这样,他在第一轮就8-10被淘汰出局。每个人都知道癌症是怎么一回事,也都被保罗感动了。当他离场的时候,所有人都站起身来为他鼓掌,并期待着有一天他可以回来。亨特妻子:我与保罗最后的日子之二坚强的他哭了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,在经历了七个月后,就在保罗要开始接受化疗前的两天,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令我们都无法相信。我们的宝贝选择在这个最不幸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我们将它这件事视作我们幸运的护身符,在黑暗中的一缕希望之光。 4月27日,保罗开始了第一次的化疗。医生给他开了一种叫做BEP的混合药物。AFP血液检查被用来确认癌症的程度,系数越高肿瘤也就越大。化疗之后,AFP的水平应当会降为正常值。但如果结果不是这样,那么就说明肿瘤无法彻底被清除。对于一个没有得癌症的健康人来说,这个系数会相当低的,从0开始最高也就到5。但是保罗的AFP结果却是24000。我们被这些数字给搞的心神不宁。他们的变化决定了我们是否可以松口气。当我第一次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时,他正戴着一个冰冷的帽子,那是一种高科技的防护帽,有利于防止头发脱落。这个情景深深震动了我,但这是真实的,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。他看上去十分地脆弱。他告诉我说,第一次戴上这个帽子让他感到十分地痛苦,他觉得头都要爆炸开了,但在那之后他的头皮便趋于麻木。 三天后,保罗回到了家。他的脸肿得就好像充了气一样。他感觉腿又沉又难受,在三天里他而且仅仅靠着输液为生。第一天要比我想象中的难熬。我以为他快睡着了,但他却整晚都醒着,非常虚弱,而我也同样辗转反侧。几天之后又有状况发生了。他的牙齿感染了,需要入院治疗,并且注射抗生素。就在我从医院看望他回到家的时候,他打电话给我,说:“你能不能过来呢,林希?”他的声音充满了渴望。 “马上吗?”我一边试着保持冷静,一边问道。 “是的。顺便带把剪子来,我的头发长出来了,乱蓬蓬的。” 他并不把脱发当回事儿,当我到达时,保罗真的显得非常高兴,因为他给我带来了些好消息。抗生素的点滴已经都结束了,而且他的AFP指数已经降到了13000。专家告诉保罗,不管第一疗程的化疗效果如何,第二疗程的化疗之后,他一定会为结果感到满意的。前两个疗程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他的指数在最后一个星期降到了590,而且CT扫描显示绝大部分肿瘤都已经被清除了。专家还表示它最终转化为胚组织瘤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。 好运还在继续。到了七月,在保罗第四个疗程的化疗刚开始时,他的指数就已经将到了34,并且在最后终于降到了18。不过第四疗程的副作用却非常严重。保罗非常虚弱,无法去参加他妹妹在塞浦路斯的婚礼。这是我们到那时为止最糟糕的一天。当她在几千英里外举行婚礼的时候,保罗的并且却在36小时内严重了很多。 由于不断的呕吐,他的口疮非常地严重。而且他的情绪也降到了我见过的最低点。我可以听到他在浴室中恶心得想要呕吐的声音,但是他却什么都吐不出来。然后我听到在那里低声啜泣。“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,”他说。“但是你还是那样的迷人,宝贝,你可以为我带来快乐。”我告诉他说。“我这样子看上去很迷人?”他忍住泪水反问道。我不忍去看他,但我最终还是看了。 他已经非常消瘦了。他已经没有了头发。他显得老了很多。他的眼睛深深地凹陷了下去。他体重降了很多却浮肿得厉害。他的手和手指已经变得非常迟钝。他浑身冰冷却还冒着汗。病痛让他一边的脸已经肿起来了,眼睛充血。他的血管已经被破坏,我可以看到他全身遍布的一条条的血管。 我回想起当初我们结婚的那天,那仅仅是一年之前的事情。当时的保罗看上去是那么的英俊,而我也为他感到骄傲。他有着飘逸的长发,阳光照在他身上,他看起来是那样的珍贵而完美。我没法在控制自己了,我开始哭泣。我们就坐在那里,一起坐在浴室里,一直在哭泣。所有的忧虑与安慰,所有的恐慌与希望,在那一瞬间全都爆发了出来。 第四个疗程结束后,我们去了Rhodes度假,就好像第二次度蜜月一样。很多时候,我们都可以真切地感到我们的孩子就在那里,因为保罗总是摸着我的肚子,每天都对着它说话。当我们回去是,医生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。我们走之前进行的血液测试显示,保罗的指数有上升到了5000。更多的化疗被提到了日程上来,不过却要尝试新的途经,因为保罗的身体已经产生了抗药性。 他被打垮了。他流着泪,仿佛世界末日已经到来。我无法接受这一切。我之前从未看到他这样。保罗在九月份又开始了化疗。每三个星期一次,就这么一直到了06年的一月。每一步走得似乎都要比之前更加困难。他的脚此时已经非常冰冷,他不得不始终穿着保温袜。 他的睫毛已经都脱落了,因此他的眼中总是会有些脏东西,我不得不时常帮他清洁一下。如果要你说一样你必须要有的东西,你肯定不会想到是睫毛,直到你失去它们斯诺克一个新的赛季又开始了。10月9日,保罗勇敢地去普雷斯顿大厅参加了比赛。在整个的05/06赛季,他没有缺席一场赛事,尽管当他走上球桌时指尖已经完全没有感觉、也没有了头发、胃痛、穿着保暖袜而且日渐消瘦。 11月时,化疗正进行到一半,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他的癌细胞指数。虽然下降了一些,但仅仅是降到了2200。 当医生告诉我说保罗仍然还需要在12月进行化疗时,我退缩了。这到底要一个人付出多少代价? 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,保罗都在我的眼前一天天的倒下去。这非常可怕,令我感到很无助。 圣诞节假期让我们暂时得到了些喘息。12月26日,EvieRose出生了。在无尽的黑暗与对死亡的恐惧中,在承受着痛苦和焦虑的同时,我们迎来了新的小生命。 那之后的第一个星期,我们一家三口时刻都在一起,几乎足不出户。如果我可以重新将那个星期找回来,我将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 但是到了1月3日,医生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坏消息。化疗已经不起作用了。这会是保罗的癌细胞维持在一定的数量,但却并不会再减少了。继续化疗已经毫无意义。 “我们能不能另想想其他办法?”我哽咽着问道。医生看起来十分地为难,因为他们已经试过了所有的方法。“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静观其变吧。”他说。 我被吓到了。我决定去找寻一些偏方,换一种方法,说不定会有所帮助。史蒂夫-戴维斯,一位斯诺克球手告诉我们说,他的一个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亲戚曾经用Essiac茶来帮助他治疗。 这种茶由牛蒡根、羊酸模、滑榆和土耳其大黄为原料,是美洲土著人的偏方,在70年前被一位加拿大的护士重新开发了出来。 我仔细地根据遵循着处方来配药,这花费了我不少的时间,但很遗憾保罗没有坚持到可以喝上一口。 到了4月,医生建议保罗再接受一次化疗,并结合服用奥克赛铂和卡培他滨。但这却导致了保罗强烈的呕吐。 6月27日,他的病再次发作了。保罗的感觉糟透了。他按着胸口呻吟道:“林希,一切又回到了起点。”接下来的血液测试证明了这一点:他的癌细胞指数上升到了40000。扫描后的结果显示,他的癌细胞又开始了增长。 医生决定再次给他进行化疗,这是最后的希望。保罗在夏天里体重下降了很多,始终非常虚弱。有很多次,他甚至无法把头从沙发上抬起来。 他的腹部胀得厉害,看上去就好像怀孕了一样。他没办法连续睡上超过一个小时,他非常虚弱,一点胃口也没有,就连我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培根三明治也不行。 最严重的事,他的皮肤开始变得暗淡无光,而且非常疼痛,因此我甚至不能总去拥抱他。在那个疗程结束后,保罗的指数依旧持续上升。我们所有的办法都用光了。在9月和10月,保罗由于过度呕吐引起了脱水,一直呆在医院。 当我第二次去看望他时,我被惊呆了,因为他已经坐上了轮椅。他的眼睛凹陷下去,他脸色苍白,皮肤失去了弹性,不知为什么他的牙齿在他的脸上会显得那么突兀。 “我要死了,林希。”他说。“我知道,我亲爱的,我知道。”我回答他,而他也开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。 这是我第一次无法说出那句话:“你会好起来的。”当我向他解释他要被送往医院的原因时,我想他已经释然了。他已经经受了太多,够了。他所希望的就是好好地睡上一觉。 10月9日晚上差5分8点,在家人的陪伴下,保罗走了,离他的28岁生日仅仅还差5天。我很清楚,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。 没有人哭泣,大家都出奇地平静。我把他的耳钉摘了下来。从他进入医院的那天开始,我就一直戴着这对耳钉中的另一枚。我还穿上了他已经穿了几个月的白色睡衣,因为那上面仍然有他的味道。 葬礼在10月19日举行,送行的人非常多。我在他葬礼的留言簿上写到:“保罗,你是独一无二的,永远都是。我的心将永远与你在一起。” 我无法形容我对他的思念,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是那样的坚不可摧,会永远地持续下去。 我要谢谢他给了我Evie,她是保罗生命的延续。感谢他带给我的朋友们。感谢他给了我美好的回忆以及因他而起的所有事情。 我会将他的爱在我心里永远保存。如果一切可以重来,我还要对他说:“我依然会选择你,宝贝。我依然会选择你。”
- 06-21· 你这该死的温柔 第十七章
- 06-14· 至天使的歌
- 06-14· 很庆幸。
- 06-14· 2011叶文智携手大汉集团进
- 06-14· 《十世轮回之沧海长歌》
- 06-14· 你这该死的温柔 第十八章
- 06-14· 大盛游泳二月份
- 06-08· 耐克和李宁在中国的错位
- 06-08· 耐克代工厂环境恶劣 卧底
- 06-03· 北京西风东韵设计公司是
- 06-02· 倬亿国际贸易网——江门
- 06-02· 明成化粉红胎天字罐一对
- 06-02· 《东坡七集》清光绪端方
- 06-02· “公开的豹子地毯不是明
- 05-31· 2009年10月4日
- 05-31· 2009年6月25日
- 05-31· 伦德保罗
- 05-31· 广西《大山河》观念行为
- 05-31· 广西《大山河》观念行为
- 05-31· 【原创】反对“把绩溪划